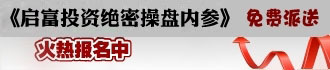股市百亿富豪尉文渊起底
时间:
尉文渊身家超80亿
主板第一高价发行股华锐风电大股东之一,上海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以90元/股的发行价计算,尉文渊名下华锐风电股权的市值将超过80亿元。
时光倒回1990年12月19日,这天尉文渊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第一声开市锣声。其时,他年仅35岁,被称为“全球股市最年轻的总经理”。作为中国早期证券业一号主角,他亲身参与并书写了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得到了其他人不敢企及的个人荣耀。但在1995年2月出现的国债期货327事件,尉文渊因负“监管责任”,离开了他一手创建起来的交易所。离开后,尉文渊选择了个人创业的道路,十几年来,他先后参与了多个公司的创业,在市场上载沉载浮,但他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开路先锋所创下的业绩一直没有被人们遗忘。
中国最大的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华锐风电在昨日的二次上会中顺利过会,这家由上海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尉文渊投资的企业是目前全球第三大风电设备制造商,而尉文渊亦将因该项投资身家或超过50亿元。
这是华锐风电的第二次上会。今年3月华锐风电向证监会递交了上市申请,预审之后,曾定于10月27日上会审核,但在审核前一天,证监会指“鉴于华锐风电尚有相关事项需要进一步核查”,决定取消对该公司发行申报文件的审核。
华锐风电受到资本市场关注,还与其股东有关。上交所原总经理尉文渊和原南方证券总裁阚治东均在早期介入这一公司。
依照华锐风电首次招股书披露的22家法人股东的股本构成看,若其上市发行的静态市盈率30倍,对应发行价62元,将有超过33名自然人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其中,董事长韩俊良合计持有1.2亿股,约合市值74亿元之多。紧随其后的是尉文渊,其控股85%的西藏新盟持有华锐风电1.05亿股,尉文渊因此间接持股8925万股,价值55亿元。
他们,从中国资本市场坐标系的原点开始,一点一点尝试,一步一步磨练,亲身经历了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进程。他们,用自己的胆识和见解推开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启动之门,引领着市场画出了一根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A股进化曲线。而同时,他们也为自己无可参照的超速“成长”,付出了代价。
尉文渊,上海证券交易所创建人之一、首任总经理。1990年12月19日,他敲响了“中国股市第一锣”。其时,他年仅35岁,被称为“全球股市最年轻的总经理”。作为中国早期证券业一号主角,这位全世界最年轻的交易所总经理亲身参与并书写了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得到了其他人不敢企及的个人荣耀。
在这条同样布满荆棘与暗河的道路上,原本前途无量的尉文渊,因“327”国债事件受牵连,最终告别了这个市场。
创建中国大陆第一个证券交易所
尉文渊出身于军人家庭,15岁时曾在新疆伊犁当兵,复员回上海后当过电影院的服务员,在上海某区委做过政法工作。恢复高考后,他考入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到正在组建中的国家审计署工作,一年后被提拔为副处长,随即又被提拔为人教司处长,可谓少年得志。
虽然仕途顺利,尉文渊对沉闷的机关生活心有不甘,一直向往着更具有挑战性的使命。他得到了人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的赏识,被调到金管处任副处长时,年仅35岁。
1989年11月,中国政府批准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人行上海分行为之成立了筹备小组,由金管处处长牵头,而金管处的工作就由尉文渊负责。
一心想做出点成绩的尉文渊主动请缨,他还向领导立下军令状——保证上交所年内开业。还剩下半年时间,筹备工作此时已经到了分秒必争的阶段。“当时,我们都替他捏把汗——即使是搬个家,新房子装修也还得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而这可是举世瞩目的中国大陆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一位当事人回忆说。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终于赶在年底开业了。从开业第一笔交易起,上交所就跨入了无纸化的电子交易时代。交易所建立起来后,对这个市场的不理解和不知道怎样去做仍然困扰着他。而他嘴里的这个“野孩子”,以惊人的速度疯长起来。
早期的上交所不可避免地烙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在早期股民中,流传着很多关于老尉和股市涨跌的经典段子。股民老许回忆说,曾有几次股市跌,尉文渊走到交易大厅一叉腰说“这个市场不会跌了,要涨了”,市场果然就涨上去了。
本计划在今日接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的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锐风电”)IPO(首次公开发行)事项,将暂缓上会。
证监会发审委昨晚发布公告称,鉴于华锐风电尚有相关事项需要进一步核查,决定取消发行申报文件的审核。按照惯例,证监会未说明暂缓的原因。
公开资料显示,主营大型风力发电机组开发研制、生产及销售的华锐风电,本次拟通过上交所发行10510万股新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46%),所募34.47亿元资金将投资“3MW级以上风力发电机组研发项目”、“3MW海上和陆地风电机组产能建设项目”和“海上风电机组装运基地建设项目”三大风电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华锐风电是于2006年2月设立,至今仅四年多时间,却已成为国内风电设备领域的“一哥”。
2009年,华锐风电的国内市场份额达到25.32%,已上市公司金风科技(002202)则以19.72%的市场份额紧随其后。
华锐风电的招股书申报稿也显示,该公司2007年至2009年的净利润分别为1.27亿元、6.31亿元和18.93亿元;去年实现每股收益2.06元;今年上半年共实现净利润12.74亿元。
也因此,随着该公司近日上会消息传出,该公司成为各方关注的明星企业。
而华锐风电之所以成为近期最亮眼的拟IPO公司,也因其发起人股东里“星光熠熠”。
据华锐风电介绍,由于任何股东均无法依据持股比例或通过决定董事会多数席位的方式对公司进行实质控制,因此华锐风电自设立起即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华锐风电招股书申报稿显示,大连重工集团目前以20%的持股位列第一大股东,其余股份则大多由创投机构持有。
事实上,在本次欲登陆资本市场之前,华锐风电便已被投资者所知悉,皆由这些创投的“大佬级“管理人而来。
国内证券业“元老级”人物的尉文渊目前通过西藏新盟间接持有华锐风电11.67%的股权,同样资深的阚治东曾于2005年12月至2006年4月短暂担任华锐风电副董事长一职,目前阚治东持有32.8%股权的瑞华丰能则持有华锐风电3.97%股权。
尉文渊是上海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阚治东曾任申银证券总裁。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
“我们创办的真是个交易所吗?”
1990年12月18日晚上,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前夕。
交易所筹备组负责人、第一任上证所总经理尉文渊坐在刚刚装修完的交易大厅,心里一片茫然。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向更纵深推进的标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业将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件,全世界都在关注。但是此刻,尉文渊却忐忑不安。更糟糕的是,对此已经不能再做什么了,只有等待。
紧赶慢赶,交易系统总算准备就绪了。但既没有经过测试,更没有做过试运行,谁也不知道在实际交易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情况。在确定选择了电脑交易的大原则和技术方案后,尉文渊天天询问系统建设的进展情况,但直到快开业了,大家心里仍然没有底。
还有个大问题是清算,清算系统根本来不及搞,成立了个清算部,到时候能正常运营吗?只有天晓得。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恐怕没有人能说清楚证券交易所是怎么回事。尉文渊和他的筹备班子从没见过一家真正的证券交易所。在信息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硬是摸索着把一个证券交易所建成了。可是,随着开业的临近,刚开始时的那种懵懂无知的自信渐渐被销蚀,一个困惑挥之不去:我搞的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证券交易所吗?
没有人能给他答案。木已成舟,即使有问题,事实上,也已没有修正和调整的可能,因为明天就要开业了。
就在几天前,一次筹备小组的碰头会上,说着说着,尉文渊突然流泪了。除了极度的疲惫外,更要命的是那种茫茫然没有方向的感觉。事情搞砸了谁也负不起责任,可是你又无能为力!尉文渊说:当时他突然感到自己就像浪涛中的一叶小舟似的那样无助,不知会被甩向何方。身不由己,这种茫然的焦虑突然间把他淹没了。
这种感觉很快就过去了,尉文渊是个不会向命运屈服的人。
那一天不仅忙乱,麻烦事还多。在布置开业典礼的会场时,疲惫的尉文渊在搬桌子时压到了脚,当时就肿了起来。晚上,伤口发炎,他发起高烧来,浑身冷热交作。但明天就要开业,全世界的目光都将向这里聚焦,而所有的努力、辛苦也都将在明天见分晓。在这样的关头,尉文渊是不可能离开工作现场的。他在浦江饭店的客房里迷糊了两、三个小时,熬到天明。
18年后,2008年7月4日,早已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尉文渊坐在记者面前,回忆当年。他笑着说:现在想起来,我们这批人可真够勇敢的。
一种偶然一种命运
由尉文渊来筹办上海证券交易所,有一点偶然。
尉文渊出身于军人家庭,15岁初中还没毕业就去新疆伊犁当兵,住地窝子,在冰天雪地中经受了艰苦的锻炼。训练之余,他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和泥打坯烧石灰筑营房,极劳累的体力活,他戏称为“基建”工作。这项工作培养了他此后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一直保持着的非常明显的性格特点,就是能吃苦。18岁他加入共产党。当兵5年后他复员回上海,在电影院当服务员,他工作积极,脏活累活抢着干,年年被评为先进,不久被选到上海某区委任宣传干部。
恢复高考后,他考入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他婉拒了母校的挽留,到正在组建中的国家审计署工作,不久当了副处长。32岁时,又被提拔为审计署人教司处长。虽然仕途顺利,但他对机关里坐办公室的生活一直心有不甘,老想做一点竞争性、挑战性更强的工作。他的老师、原上海财大副院长、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龚浩成对他十分赏识,他被调到人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当了正处级的副处长。那是在1989年的11月,他还未满35岁。当时的势头和各方面的信息都很明显:以他的能力和条件,在银行系统的升迁之路将是极其顺畅的。
1990年初,为了向世界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不会走回头路的决心,中国政府宣布将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了筹备小组,由金管处处长牵头。这样,金管处的工作就由刚调来不久的尉文渊负责。
在当时的条件下,筹办证券交易所谈何容易,老处长出去筹办了一阵,进展不大。这也难怪,谁也不知道这个交易所该怎么筹办,所以绝不是个轻松的工作。1990年6月,在海外访问的朱镕基市长向全世界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年内开业。这一时间表让国内负责筹备工作的同志措手不及,顿时紧张起来。这时候,尉文渊感觉到老处长有意重回金管处,于是他提出由他去筹办交易所。就这样,国家大局与个人处境微妙地纠缠在了一起,不经意间改变了尉文渊的人生道路。而此后这条道路上的跌宕起伏,完全出乎他此时的预料和想象。
龚浩成同意了,但明确表示,你去锻炼锻炼。第一是把交易所建起来,第二是找好接替的人,然后就回银行,另有重用。而他自己的理解则是刚到银行工作,作为新人,应该多做一点艰苦的工作,为将来的发展多打点基础。
此时,尉文渊对年内交易所要开业这个任务至底有多难还没什么感觉,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交易所的分量,不知道年底开业对他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试一试!”
解放前的上海曾经是远东的金融中心。为了学习和了解什么是证券交易所,筹备组找来几位曾参与旧上海证券市场的老人座谈。但由于在战乱中,中国的民族工业没有很好地发展,旧上海的证券市场也没有很好地运作,且这些老人只是一般的参与者或工作人员,虽然热情很高,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调研了一圈,尉文渊仍然一头雾水。
有一件事让他感觉踏实了一点,就是先要找个交易场所。这是件很具体的事情,尉文渊一下子感觉到把事情做实了,不再那么茫无头绪。
证券交易所的房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尉文渊在一本书的封面上看到过一张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的照片,于是就一心想找这样一个大厅。他每天坐着公交车到处找大厅的时候,心里仍然不清楚这个大厅该派什么用处,席位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他找过汉口路旧上海交易所的旧址,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的旧仓库,看了北京东路的火车站售票大厅和金陵东路的船票售票大厅,都失望而归。绝望之中,有人说北外滩的浦江饭店有个大厅。已经不抱希望的尉文渊冒着中午的太阳步行来到浦江饭店。这个饭店是一幢已有150年历史的欧式建筑,以前叫理查饭店,虽然已很破旧,但那气势还在。尉文渊眼前一亮:就是这里了!
有了场地,该怎么交易呢?尉文渊从很少的一些资料中了解到,国际上发达国家的交易所主要是口头竞价交易。中国人熟悉的《子夜》里描述的就是口头竞价,打手势配合高声喊价。听说像新加坡、台湾等新兴市场正在推行计算机交易。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方式的选择,很多人包括一些领导都赞成口头竞价模式,因为当时就那么几只股票,交易会很冷清,口头竞价能够满足需要,还能造点气氛。但尉文渊觉得,现在高科技发展那么快,难道我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建的交易所,还要重复那种古老的方法吗?他向领导提出,让我们试一试电子计算机交易。
尉文渊从向人民银行借的500万元筹备金中挤出100万,决定搞计算机交易系统。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口头竞价交易方式的准备,还请在美国华尔街工作过的“海归”来帮助设计口头竞价的方式。搞了一段时间,比划来比划去,找不到感觉。因此,尽管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规则中规定的是口头竞价和计算机交易两种方式,其实“宝”全部押在电子交易上。可以讲,这是一种极其大胆的、跨越式的发展,因为我们连最简单、基础的交易方法都没有掌握,一下子就进入电子交易领域,谁也不敢保证此事能够成功。他邀请当时的上海财经大学的助教谢玮,在深圳黎明工业公司的支持与配合下开始了计算机交易系统的开发和建设。难度可想而知,因为当时他们连交易所的交易规则是怎么样的都搞不太清楚,要在这个基础上编写电脑软件和程序,确实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
到11月份,交易所的筹备大体定型,尉文渊才终于有机会第一次到香港证券市场考察。尉文渊出去的头两天,他对香港联交所的交易体系看不太懂,心想,糟了,自己搞的那套东西不太一样,心情有点慌张。几天后,他突然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电脑交易的设想已经走在了联交所交易系统的前面!
上交所从开业的第一笔交易开始就跨入了电子交易时代,这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这样讲,没有电子交易的技术基础,中国证券市场不可能以这样快的速度扩张,也无法支持现在遍及全国城乡、数千万投资人参与、每天几千亿的成交规模。在电子交易的基础上,尉文渊也顺便解决了股票无纸化交易的问题,在当时,这又是一项具有世界领先意义的创举,推动和支撑了此后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
敲响开业锣声
交易大厅的装修布置、交易规则的制定、会员和席位的明确、交易员的培训、交易清算的程序、上市公司的准备等等,都在同步进行。具体到交易大厅的色调、交易柜台的位置、显示屏的安装等,尉文渊都是事必躬亲,千头万绪,忙乱不堪。
他说,那时候他白天在外面奔忙,晚上回到筹备组办公室与吴雅伦等筹备组的人员讨论交易所章程、交易规则、上市规则等文件。按照原定的日程,交易所应该在12月14日左右开业。12月3日,朱镕基来视察,交易大厅门外基建工地一片狼藉。下了车,朱镕基脸色铁青。但当他走进大厅时,脸色舒缓了下来,他看到大厅里已经布置就绪。他问尉文渊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的。尉文渊说装饰包厢的圆拱形玻璃配不到。朱镕基立刻说:你找耀华皮尔金顿,就说是我朱镕基说的,叫他们马上定做。后来朱镕基又对他说:你敢不敢大胆管理?尉文渊说,敢!
朱镕基视察过后,地方部门对交易所筹建工作的配合力度更大。开业前一天晚上,区里的市政、绿化、环卫等部门的施工队伍齐集现场,统一指挥,分批鱼贯进场施工。一夜之间,浦江饭店门外的马路和环境焕然一新,就像变戏法一样。
由于要等香港行政司邓莲如女士率领的代表团参加开业仪式,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业推迟到12月19日。
19日一早,尉文渊起床后发现,脚肿得根本穿不上鞋,只好向人借了一只大号鞋。他穿着一只大一只小的皮鞋,由人背着来到现场,一瘸一拐地在现场做最后的布置,然后倚着墙迎接贵宾。
按照原定程序,上午11点正式开始交易,由交通银行董事长、也是交易所的理事长李祥瑞授权尉文渊鸣锣开市。11点整,兴奋的来宾们还在议论着参观着,未能全部进入仪式现场,而显示屏已经开始显示交易数据。情急之下,尉文渊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第一声开市锣声。
放下锣锤,他艰难地走进电脑房,看到谢玮他们兴奋地抱在一起跳啊跳。交易成功了!
午宴上尉文渊没吃几口饭。送走来宾后,他就一头倒在了床上。此时他高烧已达40度左右,当晚被送进医院。他在医院呆了一个月,才被允许出院。有人问他开市第一天的感觉。他说:没有感觉。第一天是怎么交易、怎么收市的我都不知道。
在交易所成立后的三年中,尉文渊进行了多项尝试和改革。比如,市场扩容。到1992年底,上市公司数量从最初的“老八股”扩大到近60家。比如,扩大交易席位。交易所的会员已经从16家扩大到100多家,交易席位由最初的50个扩大到上千个,到93年更是达到了6000个。另外,他还推出一项极其大胆而有远见的金融工具创新:国债期货。国债期货以及国债回购交易工具的推出,大大活跃了国债市场,提高了金边债券的声誉,极大地促进了当时让政府揪心的国债发行难问题的解决,也是资本市场深化发展的一次勇敢探索。但也正是三年后的“3·27”国债期货事件,让尉文渊因负“监管责任”而离开了他一手创建起来的交易所。
尉文渊目前是新盟集团董事长。集团从广告业做起,已拥有庞大的资产和投资,创业投资特别是风电项目的投资是最让人瞩目的一块。
“在中国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下搞出一个证券交易所发展资本市场,绝对是一项重大的制度突破,这个政治智慧和决策应该得中国经济改革大奖。”这样说的时候,历经了几多风雨的尉文渊豪情不减当年。
小资料
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加快开发、开放浦东地区的十大政策,决定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其中之一。
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大会,审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章程,李祥瑞为第一任理事长,尉文渊为第一任总经理。
1990年11月2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上海市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
1990年12月31日截至1990年底,沪市共有8家上市公司,俗称“老八股”。上证综指当年最低95.79点,最高127.61点。(周松林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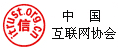
郑重声明:本站所载文章、数据仅供参考,使用前请核实,风险自负。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深圳市启富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证监机构字(2001)195号,资格证书编号:ZX0152]
[公司营业执照] [公司证券投资咨询资格证书][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
服务热线:400-678-1178 0755-82718153 咨询QQ: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康路卓越梅林中心广场(北区)2栋601室 备案号:粤ICP备11044237号
版权所有:深圳市启富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